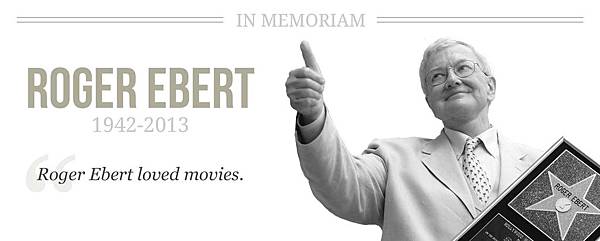
我已經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開始看Roger Ebert的影評了,只知道有這麼一天,他那比著大拇指的網站就這麼待在我的電腦資料夾裡,點開網頁閱讀他的文章,未必每次都能認同他對某部電影的觀點,但是不管認同與否,都能在他的文字中得到智性上的滿足,從來沒有一次感到失望過。
這篇文章摘自Roger Ebert的影評集《偉大的電影》裏頭的序。每次讀這篇文章都深深覺得感動,Ebert不僅寫出了我們為什麼這麼喜歡看電影,他還告訴我們如何觀看電影才能成為一名好的觀眾,而好的作者往往也是位精明的觀者。
可惜Ebert的著作在台灣並無譯本,只能買得到英文以及對岸的簡體版本。一個字一個字的閱讀並打下這篇序文,如果真的喜歡電影、想要研究電影的人,讀到最後一段:
「電影看多了,不知不覺就會把導演們當成老朋友,對他們的好惡瞭若指掌:布紐爾對人性的厚顏無恥最感興趣,史柯西斯關注宗教罪惡感的無底深淵,黑澤明歌頌身處於充滿敵意的大環境下的個體,懷德往往震驚於人們為了追求快樂而做出的舉動,基頓表現的是人的意志如何挑戰物理條件的限制,而希區考克創造的影像猶如醉人的夢魘。每一個熱愛電影的人最終都會抵達小津安二郎的視界,從而領會到電影的本質並非運動,而是運動與靜止之間的抉擇。」
我想都會對Ebert的文字深深地感到著迷。
Ebert在三年前帶著他那令人難忘的大拇指過世了,但是他的網站仍然聚集著一群作者持續透過他的方式閱讀電影,寫作影評。Ebert對電影的觀點在現在讀起來也不覺得過時,這些文章就靜靜的躺在他的網站裡——和那些經典的老電影一樣,等待影迷們的發現。
《偉大的電影》序
Roger Ebert
我們生活在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盒子裡,電影則是盒子上的窗口。電影允許我們進入他人的精神世界-這不僅意味著融入銀幕上的角色(儘管這也很重要),也意味著用另一個人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法蘭索瓦・楚浮(François Truffaut)曾說,站在一個電影放映廳的前端,轉過身去看著觀眾沈醉在光影中的面孔,此情此景對一個導演來說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如果電影還不錯,觀眾們的臉上就是一副魂不守舍的表情。在這短暫的一刻,他們游離於另一個時空,為別人的喜怒哀樂而感動。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最能喚起我們對另一種經驗的感同身受,而好的電影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
然而,真正的好電影並不多。有些週末場的影片還算湊合,至少能讓我們消遣兩小時,影評人(包括我自己)也會根據這些片子的娛樂價值對其加以品評。我們花錢買票就圖個樂子,這類影片通常也能讓我們樂一樂,但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收穫可言了。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好萊塢已經進入一昧追求市場效益的階段,而全球電影又被好萊塢機制所統治,所生產的影片專以糊弄低端口味的觀眾為目標。2001年愛丁堡國際藝術傑上,西恩・潘(Sean Penn)對觀眾說:「要是一部片子裡表達了三個觀點,那就算壞了規矩,這片子也就沒人看了。」而本書所介紹的影片每一部都表達了至少三個觀點。這一百部影片不一定就是電影史上最了不起的一百部,因為真正的傑作是無法排行歸類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佳片榜單都是愚蠢之舉。但是不妨這麼說:如果你想縱覽電影誕生後第一個世紀內的里程碑之作,那麼請以本書作為起點。我最初開始撰寫這些影評時,好萊塢的新片質量正在不斷下降(現在降得更低了),而大批年輕的電影愛好者又對電影史知之甚少。自1968年以來,每年春天我都會參加在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多分校舉辦的世界事務大會,並在會議期間主持為期一週的電影研討會,每期觀摩一部電影。與會者坐在黑暗中,利用暫停-播放功能細細觀看影片,有時甚至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研究。最初我們放的是十六釐米底片,後來有了VCD和DVD,放片子容易多了。在場所有的人都積極參與討論,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景:屏幕上的影片定格在某一幅畫面,黑暗中充滿了民主的氣氛。最初幾年我放的主要是經典老片,例如《大國民》(Citizen Kane,1941)、《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1949)、《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1960)、《將軍號》((The General,1927)、《美人計》(Notorious,1946)、《假面》(Persona,1966)、《生之慾》(生きる,1952)、《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1976)等等。這些年來,隨著電影協會紛紛衰亡、家庭影院逐漸興起,學生們對昔日的經典越來越不感興趣。有一年,我提議看《迷魂記》(Vertigo,1958),他們卻一股勁兒地求我放《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1999)。結果是這兩部片子我們都看了。我承認《鬥陣俱樂部》技術高明,無數影迷寄給我的電子郵件也讓我知道影片給他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仍然難以贊同這部片子。花了一週的時間細看《鬥陣俱樂部》之後,我對其拍攝技巧更加欣賞,對其思想內容卻更加不屑了。這部電影主題鬆散,缺乏智力上的統一,但這個缺點並沒有影響整部影片所獲得的好評,因為在眼下這個時代,觀眾已經深陷音響效果和動作效果的包圍之中,電影鏡頭越來越短、聲音卻越來越大,特殊效果搶了主題和表演的風頭,甚至取代了後者的地位。今天的觀眾正在逐漸失去進入電影敘事弧的能力,他們還有那個耐心等待《黑獄亡魂》中哈利・萊姆的出場嗎?
在波爾多大學以及其他高校和學生們交流時,我發現不少大師的名字已經無人知曉了。甚至連電影專業的學生都沒有看過布紐爾(Luis Buñuel)、布列松(Robert Bresson)或小津安二郎的任何一部影片。他們頂多看過約翰・福特(John Ford)或是比利・懷德(Billy Wilder)的一兩部片子,知道六七部希區考克的經典之作,會向《大國民》屈膝致敬,對星戰系列爛熟於心,有時還會來上這麼一句:「我不喜歡黑白片。」這句話顯示出他們無可救藥的庸俗。本書列出的一百部影片中有六十部都是黑白片,另有三部既用了黑白膠片又用了彩色膠片。如果你想了解電影的歷史、想真正愛上電影,就一定要了解為什麼黑白電影的效果不但不比彩色效果差,而且可以比彩色電影更加豐富。
我逐漸發現,對於許多電影愛好者乃至最狂熱的電影愛好者而言,早期經典電影仍然是一片尚未開發的領域。作為一家日報的影評人,我不想一輩子只把眼光放在當代影壇。1997年我拜訪了當時在《芝加哥太陽日報》擔任編輯的奈傑爾・韋德,向他提出開設一個雙週專欄,以較長的篇幅回顧過去的經典老片。他表示了支持。作為一個編輯而言這是很難得的,因為絕大多數美國電影期刊都把重點放在名人花絮、票房紀錄等迎合底層需求的欄目上。從此以後,我每隔一週就會重溫一部老片,而讀者的反應令人鼓舞。我收到過資深電影愛好者寄來的信件和電子郵件,與其他影評人展開過辯論;一位大學校董事會成員和一位來自麥迪遜市的少年都向我發誓要看遍我列出的每一部影片;圖書館媒體項目則以折扣向大眾提供這些電影的DVD影碟。
與當代大片相比,經典老片很難受到注意,這與電影協會紛紛衰亡有直接關係。在家庭影院興起之前,所有的高校、大多數公共圖書館和社區中心都設有電影協會,這些協會常常放映優秀的16釐米底片電影,而且收費相當低廉。我就是在伊利諾大學的兩個電影俱樂部裡獲得了最初的啟蒙,在那裏我看到了許多原本不會主動去看的片子。就在大學的教室裡,我第一次觀看了《生之慾》、《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梟巢喋血戰》(The Maltese Falcon,1941)和《搖擺樂時代》(Swing Time,1936),當時我對這些影片的背景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門票僅售二十五美分,而且看完之後大家會聚在學生會裡,一邊喝咖啡一邊談論剛剛看過的片子。
從理論上來說,家庭影院的興起應該給熱愛經典影片的人帶來了福音。的確,本書中所列出的名作幾乎都有不同版本的影碟,大多數人也都必須通過這種途徑才能看到這些影片。但當你走進自家附近的音像連鎖店時卻發現,門口的展覽架上力推的總是最新的好萊塢票房大片,你必須在角落的陰影裡徘徊許久才能找到“外國影片”或是“經典影片”一欄,而且其內容往往少得可憐。獨立音像店和網路營運平台(例如netflix.com、facets.org等)提供的影片種類較多,但一般的影迷能找到這些地方嗎?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史坦利・考夫曼發明了一個新詞彙——“電影的一代”(the film generation),專指一批對電影十分狂熱的年輕影迷。我本人就是那一代人中的一個,我可以作證,我曾經在普通影院門口排隊等候觀看雷奈(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61)和高達(Jean-Luc Godard)的《週末》(weekend,1967),這些影片在那個年代大受歡迎,場場爆滿。而在今天,就連最流行的外國翻譯片在國內也得不到影片發行壟斷行業的青睞,主流電影專門瞄準男性青少年這塊市場,能讓影院門口排起長隊的只有好萊塢最新的拿手好戲——用A級片的預算拍出的B級片。
本書列出的電影中有許多部我都看過十幾遍,其中有四十七部我曾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研究過,但著手寫作每一篇影評之前,我仍然要將影片重新看一遍,因為這才是我最重要的目的。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國影評人德瑞克・馬坎姆(Derek Malcolm)也曾經選出一批類似的經典影片,他說他選片的唯一標準就是一想到以後再也看不到這些片子就趕到無法忍受。在將零散刊行的影評編纂成書之前,我對它們進行了修訂、擴充,在必要的地方做了改動,例如添加了對《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1979)新出的加長版的討論。截至本書出版之前,我已經寫了一百五十餘篇影評,這本書裡只選了一百篇。我的雙週專欄仍然在刊載。
通過修訂自己多年來的影評,我逐漸意識到編寫這部書是一項多麼美妙的任務,因為它讓我回憶起了觀看每一部電影的情景。我記得某年一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在倫敦搭地鐵到漢普斯特區的人人影院看《苦雨戀春風》(Written on the Wind,1955)。在夏威夷電影節上,我和研究日本電影的資深專家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一起把小津安二郎的《浮草》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過了一遍。在維吉尼亞美國電影節,我和《蠻牛》(Raging Bull,1980)的剪輯師特爾瑪・修恩梅克(Thelma Schoonmaker)一起分析了該片(最了解一部電影的人就是這部電影的剪輯師)。在漂流電影節上,我和攝影師哈斯克爾・韋克斯勒(Haskell Wexler)共同觀看了《北非諜影》(Casablanca,1942)。在特柳賴德電影節的年度巡遊期間,我和彼得・博格達諾維奇(Peter Bogdanovich)一起在新伊莉莎白女王號郵輪上欣賞了《大國民》。我參加了《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1968)的全球首映式,後來在伊利諾大學主辦“不受好評的優秀電影”電影節時又在大銀幕上觀看了該片70釐米底片的版本。2001年的坎城電影節放映了《現代啟示錄》,影院條件堪稱世界一流。密西根州三橡樹村的威克斯影院則以牆壁為布幕,用投影機放映《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1925),觀眾坐在折疊椅上,而來自班頓港的“混凝土”樂隊則在一旁演奏他們自己創作的配樂。在“不受好評的優秀電影”電影節上我也看過《不死殭屍—恐慄交響曲》(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1922),由來自麻省坎布里奇市的“合金”樂隊配樂。我記得有一回去洛杉磯拜訪脾氣乖戾卻又深受朋友們喜愛的電影收藏家大衛・布萊德利(David Bradley),在他家客廳裡看了16釐米底片的初版《夜長夢多》(The Big Sleep,1946),如今故人已去,只剩回憶。我在威尼斯的聖馬克廣場露天看過《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影片結束之後卓别林親自走上陽台向人群揮手;儘管這部影片我看過無數遍,那次經歷卻是最愉快的一次。我第一次看《天堂之門》(Gates of Heaven,1978)是應芝加哥千面多媒體中心的米洛斯・斯塔里克之邀,當時他說有部片子一定要給我看看,卻又不肯告訴我影片的內容。這部神秘的巨作多年以來一直遭到冷落,因為人們對關於寵物墓地的紀錄片不感興趣。
看過許許多多好電影之後,你就能逐漸體會到導演的意圖,分辨出不同的風格。你會發現有些電影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有些則是集體之作。有些電影旨在突出明星,例如馬克斯兄弟的喜劇、亞斯坦與羅吉絲的歌舞片;有些電影則嫻熟地駕馭了類型片,從力求超越劍俠片模式的《星際大戰》到試圖匿身於黑色電影之列的《繞行》(Detour,1945)均屬此類。大多數好電影都旨在表現某種風格、體現某種情調或反映其創作者所建構的某種意象。一位電影導演會在某一點上觸發你的想像力,激起你對其他作品的渴望。電影看多了,不知不覺就會把導演們當成老朋友,對他們的好惡瞭若指掌:布紐爾對人性的厚顏無恥最感興趣,史柯西斯關注宗教罪惡感的無底深淵,黑澤明歌頌身處於充滿敵意的大環境下的個體,懷德往往震驚於人們為了追求快樂而做出的舉動,基頓表現的是人的意志如何挑戰物理條件的限制,而希區考克創造的影像猶如醉人的夢魘。每一個熱愛電影的人最終都會抵達小津安二郎的視界,從而領會到電影的本質並非運動,而是運動與靜止之間的抉擇。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